《千与千寻》重返大银幕请干了这碗叫“宫崎骏”的鸡汤
2019年6月,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18年前的旧作《千与干寻》在中国上映,起用了周冬雨、井柏然、彭昱畅、田壮壮这样的神仙组合为其配音,上映仅8天后,票房已超过3亿人民币,毫无悬念地碾压了同期上映、同样打“情怀牌”的《玩具总动员4》。
即便这两年老片重映已渐成风潮,但《千与千寻》仍是特别的。这部被很多人归为“有生之年系列”的影片,是官崎骏的巅峰之作,曾获得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也是至今唯一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的非英语动画影片,同时还获得了第5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18年前在日本上映时,这部影片就创造了日本动画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形容也不为过。

宫崎骏和他的电影王国开创了一个不同于迪斯尼风格的动画电影新流派,让我们对动画的关注真正超越了技术层而的探讨,打破了动画导演和电影导演之间的“阶级”壁垒。并且让这种美学精神不止于动画,而是延伸到文学、旅行、艺术、环保等各个领域。难怪有人说:在这个情怀已经变得廉价的年代,官崎骏通过共情,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更高级的感染力。
共情让“鸡汤”不廉价
在日本文化研究学者、塔夫茨大学教授苏珊·纳皮尔(Susan Napier)的著作《宫崎骏的世界:艺术人生》中,答案是肯定的。宫崎骏的作品甚至可以当作社会学的研究教材,因为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
“风之谷”谴责的是科技进步带来的灾难《龙猫》宣扬回归乡村生活;当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来到东京谋生,《魔女宅急便》便给大家讲了一个在大城市里奋斗的小女孩的故事;当日本的家庭危机越来越严重,《哈尔的移动城堡》便诞生了…一当动画变成挽歌,宫崎骏也便成为了一种情怀,一种共鸣,抑或一个文化现象。
宫崎骏在1960年代正式开始了他的动画生涯,当时日本经济崛起,并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几乎同时,经济发展也迅速地毁灭了日本的乡村和乡村文化。以至于有的人说,宫崎骏这一生好像只拍了一部电影,就是表达对现代日本的诸多不满:遗忘历史和传统、迷信科技、打压女性赋权、理想家庭关系的幻灭、对自然的过度索取。而这些,不止日本,整个世界都在经历着。
一片连绵起伏的草地,点缀着鲜花,天空被高高的积云遮蔽,岩石覆盖的山麓向白雪覆盖的山峰延伸,森林边缘有逐渐黯淡的光线—— 一切都是官崎骏式的。怛动画只是它的壳,他太善于用套路化的场景展示精神上的东西,而且大多数时候展示的恰恰是我们精神上没得到的东西。
当汤婆婆夺走每个人的名字,是否意味着你找不到了回家的路?当《幽灵公主》把失落感演绎到极致,你是否也会思考入与自然之间的脆弱关系?当金鱼姬无法变成人类,宗介如何信守最初的承诺?这种共情,让宫崎骏熬制的“鸡汤”绝不是廉价品。
宫崎骏的电影,往往一半是幻想,一半是冒险,一半是梦想,一半是隐喻。影迷们也执着于探索宫崎骏影片中的各种隐喻,比如认为《千与千寻》反映的是日本儿童卖淫的现象,澡堂在日本江户时代就是妓院的掩护,片中所有的神都是男性。
对此,导演给出的回答也耐人寻味:“我认为象征现代世界最合适的方式是性产业。难道日本社会没有变得像性产业一样吗”;影迷暗戳戳地比对故事的时间、地点、情节,坚信《龙猫》影射的是1960年代女学生被杀的狭山事件,好在吉卜力工作室最后发了声明否认;《幽灵公主》其实描绘的是麻风病……
好在这位特别拧巴、极度悲观的导演,又足够善良,所以“红猪”才能化解一个男人的中年危机,《风之谷》里才会和怪虫和解,《天空之城》才可以继续飘浮。还记得《魔女宅急便》里的琪琪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不能飞,我就什么都不是。是啊,在都市生存的人何尝不害怕失去身份认同。在官崎骏构建的虚幻世界里,那些绝望沮丧的心灵,那坐被现实磨平棱角的人,得到了片刻的喘息和治愈。 在很长一段时间,动画是被迪士尼和梦工厂统治的。它教导女性,应该像淑女一样,嫁给一位王子,并在父权社会中幸福地生活。但在日本,动画是一种不专门针对儿童的流派。戏剧、浪漫、情色,甚至哲学一一它可以无所不包。
宫崎骏的作品,更接近欧洲文学中的童话,这些童话可以被视为儿童即将进入现实世界的成人礼,也可以看作是让你重遇你身体里的那个孩子。成长永远是张单程车票,有去无回,但路,可以我自己来选。
东方审美的胜利
《千与千寻》的结尾,汤婆婆放了千寻和她的父母,他们坐上车,来到了一个新的城镇。白龙却留在了那个神灵的世界,并嘱咐千寻“不要回头”。
但是迪斯尼担心美国人无法接受这个结局,在美版公映时,他们加了一个画外音,千寻的父亲说:“哇,新学校,新城镇。”千寻说:“我想我能行。”
在1906年出版的《茶之书》中,日本著名作家、美学家冈仓天心问:西方什么时候才能理解东方?“我们从来不吃莲花和蟑螂”,同时“西方人也没有‘浓密的尾巴…。看来,过了一个世纪,东西方文化上的结界仍然存在。
日本人天生执迷于表达美丽事物的短暂性。无常的美、不完整的美,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并且诞生了诸乡术语,例如“物哀”“佗寂”。它们背后承载的情感含义,很难准确翻译。就像日本最著名的神社伊势神宫一样,每隔20年就要被拆除,再用原材料重建一次。这种美虽脆弱,却为观察者创造了一种强大的体验。

官崎骏深谙此道,并且可以把淡淡的忧伤具象化,再打上独特的个人标签。但这其实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我们东方人特有的情绪。西方,尤其是美式文化,需要主人公有一个归宿,简而言之,一个happy ending,模棱两可不是一个好结局,所有的留白必须被填满。
一个好的改变是,如今,许多美国观众也在吐槽迪士尼的画蛇添足。而官崎骏的关注点本就在人性上,不同的文化背景,并不妨碍去理解影片的表达。
更难得的是,这位“愤青”呈现出来的电影从不说教。他的电影里极少有坏人。悉数美国最经典的儿童电影,世界大多非黑即白,好和坏分立两大阵营。电影中结尾,往往是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或是被好人同化,改邪归正。
但宫崎骏电影中所谓的“反派”,做事动机好像也没有那么十恶不赦。他自己曾解释说:“有的电影一定要好人与邪恶的人战斗,最后有一个美好结局。但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动画师,你必须画出邪恶的形象。画邪恶的人物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所以我决定不拍电影里的坏人。”是啊,人哪有好的,只是坏的程度不一样而已。生活一一以及好的艺术——往往包括更多的灰色地带。我们身边一定也有孤独的无脸男、俊秀的白龙、任性的巨婴、贪婪的青蛙,以及时而温柔时而自私的汤婆婆、外表凶恶内心善良的锅炉爷爷。
这样的电影,是否也是为了让孩子们做好准备,去面对真实的世界呢?唯一可控的不变量是,无论真实的世界如何,保持独立、善良、创造力,总是能有意外收获。
宫崎骏还是一个东方美学金句王,多少人曾拿电影中的台词当过QQ签名啊。
“遇见过的人,此生你不会真的忘记他们。”
——《千与千寻》
“年纪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失去的很少……”
——《哈尔的移动城堡》
“大家也来笑,吓人的东西就会逃跑。”
——《龙猫》
“命运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但你可以面对它。”
——《幽灵公主》
“我们的孤独就像天空中漂浮的城市,仿佛是一个秘密,却无从述说。”
——《天空之城》
“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
——《起风了》
以至于有人打趣:在亚洲电影市场,能生产如此多金句,且金句与故事情节、影片气质相互成就的,除了王家卫和宫崎骏,再想不出第三人。
甚至网上随便一搜,还能找到许多模仿宫崎骏语言风格的伪语录。一个宫崦骏铁杆影迷曾吐槽,之前看到网上的宫崎骏经典台词中有这么一句:“世界这么大,人生这么长,总会有这么一个人,让你想要温柔以待”,出自《哈尔的移动城堡》。他自问看过不下5遍,却不记得有这句台词。出于一个宫崎骏影迷的自觉,他又找出了中、日、英三个版本的《哈尔的移动城堡》,仍然一无所获。他在论坛上给发帖人留言,得到的回复是:“这是我看到海报后,自己模仿官崎骏写的”……
如今,这种东方美学更加精炼了:日本是一个看起来像未来,但却被过去思维束缚的地方。想起十几年前,一位西方画家要为宫崎骏画像,他希望画下这位动画大师坐在桌前奋笔疾书的样子,但宫崎骏只是坐在那里,淡淡地说:“不,你可以画我走进阴影”
“一个人,要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
宫崎骏的才华从何而来,至今仍是个谜。
即便在很长一段时间,动画都被看作是取悦儿童的,但不可否认,它与电影同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最早的一部动画影片是法国人埃米尔·雷诺于1892年创作的,当时使用的是类似于投影仪的光学仪器。直到1906年,美国人詹姆斯·斯图尔特·布莱克顿才用“逐格拍摄”的手法,制作出了第一部现代动画片:《滑稽脸的幽默相》。
1916年被视作日本动画的元年,第一部饫篇动画在1940年代诞生,到二战后的反战题材大爆发,再到1970年代的成熟期,日本动画从未有过断代。1963年的《铁臂阿童木》,更是成为文化输出的媒介发往亚洲、北美和欧洲。
1941年,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宫崎骏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航空工程师,经营着家族企业,为三菱远程战斗机制造零部件。这种家庭环境一方面让他从小痴迷于探索天空,另一方面也让他“因内疚而痛苦”,因为他的父亲从战争中获利,战争间接给了全家人舒适的生活。
官崎骏从小与母亲关系亲密。母亲一直受肺结核病的困扰,但她自强自立并且勤奋好学,这也可以解释宫崎骏的作品中为何常以女性为主角。像1988年《龙猫》中生病的母亲、2013年《起风了》中的直子,都或多或少有着母亲的影子。
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解释了自己的艺术愿景是创造出一种美与善的视觉,去替代现今疯狂、堕落、消费主义、色情且孤立的世界。这种愿景是在宫崎骏17岁时形成的,那一年他看了日本第一部彩色长篇动画电影——《白蛇的故事》,对,就是中国的“白蛇传”。宫崎骏形容这部影片里纯洁的情感让他“潸然泪下”。在4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确抑制了自己的悲观情绪,并以一种神奇的、有趣的、高级的方式激发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保护。
宫崎骏刚开始做动画师时,日本动画的预算很低,美国动画每秒使用24帧,每帧都是手绘的,而在日本,为了省钱每秒只有12帧,动画师必须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两倍的工作。每秒的帧数越少,意味着人物就不能画得那么逼真。但反过来看,当动画剥开技术层面的外壳,赤裸裸地展示故事和气氛时,好像更能检验一部动画作为电影的优劣。宫崎骏会待在火车站好几天,只为了画好少女裙子上的褶皱,用头发的变化显示千寻不同的境遇……无论每秒多少帧,他总能通过一支笔把你带进情境之中。

1985年,吉卜力工作室正式成立,吉卜力意为撒哈拉沙漠上吹来的热风( Ghibli),同时也是二战时由意大利飞机制造商卡普罗尼开发的一种侦察机的名字。吉卜力的出现确实“在日本动画世界吹起一阵轰动的风”一一出品的8部电影跻身日本15部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之列,其中,“千与千寻”以308亿日元登顶日本票房榜首,纪录至今未破。
东京近郊的三鹰之森吉卜力美术馆,是日本最难买票的博物馆之一。主体建筑是富崎骏亲手设计的,远看像一个超大的土垤房,边缘的流线型加上粉色、绿色和黄色的搭配,像是一粒正在融化的太妃糖。内部彩色的玻璃窗、螺旋形的楼梯、屋顶上的花园、林中矗立的机器人士兵、柔软的猫巴士……这里的餐厅也别出心裁,没有聘请专业厨师,而是让一位擅长家庭烹饪的母亲掌勺。
许多细节共同造就了一种魔幻感:对自然世界的敬畏、对飞行的迷恋,以及对未知领域的好奇。正如博物馆的标语:这个世界是多么复杂,这个世界是多么美丽。
宫崎骏不仅通过电影宣传自己的信仰,在现实生活中也在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起风了》上映时,在日本再次引发了对宫崎骏政治观点的争议。宫崎骏不避讳自己的政治主张,反对战争、反对修宪,并认为应该向二战期间的亚洲慰安妇提供赔偿。一个人自始至终都能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其实并不容易。
2005年,宫崎骏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直言不讳“希望能看到东京被大海淹没,NTV(日本电视台)变成一个孤岛,曼哈顿成为水下之城,希望看到人口锐减,不再有高楼大厦。金钱和欲望——所有这一切都崩溃,杂草取而代之接管世界。”喜欢宫崎骏的人知道,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文明的终结就是他认为最美妙的事。这个用动画吸引儿童和成人的人,和抱怨人们花太多时间在虚拟事物上的入是同一个人吗?但这正是他的迷人之处。
2016年,新海诚的2D动画《你的名字》在中国热映,票房突破了5.7亿人民币,创下了日本动画电影在中国国内的最高票房。那一年,恰好是日本动漫诞生的第100年,新海诚,恰好被誉为动画大师宫崎骏的接班人。
那一年,宫崎骏恰好第7次食言,准备再次复出。这位78岁的老人,工作已经排到了2020年。对影迷而言,至少还能再看到一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之后呢?也许他会再次宣布隐退,再之后,也许他还会复出。无论怎样,官崎骏的食言,谁不是乐见其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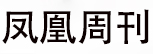
 凤凰周刊
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