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酒店社工口述:疫情中未被忘记的露宿者
新冠疫情暴发后,部分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变成了城市里的“流浪者”。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也生活着一些露宿者。与武汉情况不同,他们常年住在城市的角落里,有时是偏僻的路边,有时是废弃的大楼,或者是人烟稀少的公园。
住在室外往往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有人习惯了空旷的环境,对室内有所恐惧;有人不喜欢托养机构的限制,觉得不自由;有人爱面子,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从2014年开始,张潇和另外几名社工成立了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专注于北京露宿群体的公益服务,栗哥是后来加入的几名年轻人之一。他们接触过形形色色的露宿者,有些甚至打过好几年的交道。从云南来的露宿者老陈,曾经有无数次被救助的机会,但他都不愿意,社工们后来也不再劝说。

但在这次前所未有的疫情面前,很多露宿者第一次主动选择了向政府求助,并住进了隔离酒店内。让他们最恐惧的其实不是疾病,而是在社会长达1个月的“停滞”之后,确实没有东西可吃了。
2月9日,西城区民政局为露宿者设立的隔离酒店开始使用。陆陆续续有露宿者开始入住,测量体温,做核酸检测,每天在房间里生活。但他们并不习惯这样的封闭环境,心理压力很大。
疫情之下,一些地方的管理粗暴让张潇曾经有过担心,这些露宿者们会不会最终被强制隔离,隔离结束后将被强制返乡。疑虑的渐渐消除是从和风社工的成员们也被“调去前线”开始的,他们要安抚露宿者的情绪,帮助他们分析困境原因,再规划隔离期结束后的生活。

第一位结束隔离的露宿者在2月25日回到了街头,没有被强制返乡。社工们和救助管理机构共同给他规划了若干路径,最终还是尊重了他个人的意愿。
以下是和风社工栗哥的口述。
找不到东西吃了
我们也是除夕夜的前两天才了解到新冠疫情的严重性。原本我们这几年有一个固定的项目,是在过年的那天一起去办公室包饺子,然后送给露宿者,但今年考虑到安全以及出行是否方便的问题,取消了。
最终只有张潇在那天出了门,给一些露宿者送口罩。那些口罩是挺早之前买的了,原本是为了防雾霾的,但一直没用完,还剩了几盒,这次便临时用上了。

受制于人员、力量的限制,我们这几年的观察和服务主要局限在三环以内,包括西城区、东城区和丰台等区域。最开始的时候很容易便可以在街头发现露宿者,粗略估计大概有几千人,总有人可以交谈。
但最近几年,露宿者的数目开始慢慢减少,如今三环以内的露宿者只剩下几百人。他们不再容易被发现,寻找起来需要依靠以前的关系基础。已经熟悉起来的露宿者,是那附近的“百事通”,通过他们才能知道附近哪里住着人。
露宿的人有从外地来上访的,有想要来打工但又找不到工作的,有来看病但又被骗的,或者就是单纯的没有能力住进房子里的。但无论如何,穷困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他们之中很多人并非大家印象中简单的乞讨人员,他们强调自由和尊严,只是居无定所,平日里靠拾荒或者打一些零工来过活。
他们有的人其实是有手机的,虽然可能是很破旧的二手货。也有很多入接收信息的方式是收音机,无聊的时候就一直在听新闻。所以露宿者们也是有渠道接收到关于新冠疫情的消息,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但肯定不会特别清楚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我们是在2月3日复工的,到2月10日这段时间其实也是在家办工。但是我偶尔会出去外展,在城里走—下午,遇到认识的不认识的露宿者,都尝试着去聊聊。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其实是很少有人戴口罩的,基本和平时一样。
当然,这也跟他们设钱买口罩,或者根本没有能力像常人一样网购口罩有关。如果发给他们,叮嘱他们戴,他门也是会戴上的。
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正常的生活受影响比较大,会觉得疫情特别可怕。但对于这些露宿者来说,他们到现在可能也不会有这种感觉。没有什么是可怕的,每天吃上饭才是最大的事情。疫情对他们的主要影响是,实在找不到东两吃了。
我是本地人,每年的春节基本都是在北京过的。以往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也都回老家了,很多饭店都关门了,北京变成我们说的半个空城。这个时候露宿者是很难去饭店吃剩的或者捡垃圾来卖钱的,毕竟收废品的人也要回去过年的。
往年他们都会在春节前去超市囤点吃的,面条、馒头等,撑过一个星期。等到人都回京了,日子也就一切如常。今年过年的那一周,和往年比不会有多大影响。
但是没有预料到的事情是,现在疫情已经长达一个多月了。对他们的主要影响是,没有资源了,捡不到东西,也没有存粮了。没有钱挣,没有饭吃,这个在他们眼里可能比得病可怕多了。在空旷的室外,感染的概率也相对小一些。
很多人第—次主动报警求助
这些年我们和各种各样的露宿者交流过,最终流浪街头,其实是他们的选择。对于年龄较大,或者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他们乜可以住进救助站的托养机构。在当前的政策背景下,只要自己有意愿接受政府部门的救助,那么总有办法可以不再露宿街头的。
但前提条件是,需要露宿者自己先点头。政府的救助方针是“主动求助、无偿救助”,一旦他们不愿意,政府部门是不能强行上手的。
很多人都是过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想被拘束在救助机构里,出门需要报备,还有时间限制。还有一些人有着各种各样的不信任,对有些部门很排斥;或者还有的,说自己脸皮薄,不想给政府添麻烦。
但在这次前所未有的疫情面前,很多人第一次选择了向政府求助,因为实在是没有东西吃了。两城区民政局在2月9日专门设了隔离酒店来收纳露宿者,很多人自己就来了。当然我们也会一条街一条街地走,看到有露宿的人就去通知他们,同时也提醒他们疫情的严重性。
大部分的人其实是自己主动报警求助,或者去救助站的。我经常会在微博上刷一些关于露宿者的信息,会看到有市民拍照艾特官方,说哪里有露宿的人。他们自己也会送去一些吃的,所以其实也是想帮助他们,不是想驱赶吧。
以前我们遇到一些露宿者,也会询问他们愿不愿意去救助站或者托养机构,也会劝一劝他们。但很多人都是坚决不愿意,我们之后也不会再提,但会定期去看望他们,和他们聊夭。
比如从云南来的老陈,已经在北京飘荡了十几年了。其实他很早就没有再上访了,但也一直没有回老家。我觉得老陈已经陷得太深,他需要一个执念来支撑自己,他总告诉别人自己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政策”,但具体是什么,他也说不上来。
其实老陈有很多次机会可以住进室内,去托养机构,不用再为吃什么喝什么发愁。但这么多年他从来不愿意,而是一直住在天桥下面。
因为他对我们社工不排斥,所以这么多年来几乎都是我们新人“练手”的对象。但这次都不用劝,他自己就来了。他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老陈是2007年来北京的,“非典”的时候他还在老家呢。
隔离点是那种快捷酒店,双人间,救助站每天也会给他们送饭。老陈终于住进了室内,吃上了热饭,看上了电视,我们觉得这是他这么多年怀疑、恐惧,但又期望过的一个归宿吧。
我最近去外展,可能一下午在空旷的大街上走几万步,会零星遇到两三个露宿者。这些剩下的,其实就是根本不想去隔离酒店接受救助的人,我会劝说,但效果也不明显。他们一般都还有存粮,或者能想办法弄到吃的,觉得没有必要去。还有可能是担心后续的情况,如果去了,万一出不来怎么办呢?
“逆行”进城打工的新流浪者
西城区的隔离酒店是2月9日正式开始使用的.那一天第一位自愿接受隔离的露宿者走进去,接受了核酸检测。之后陆陆续续可能有四五十个露宿者入住。因为露宿者接触了什么人员比较难追踪,不太容易弄清楚接触过什么人,所以对他们每个人都测了体温,无论有没有发烧,都做了核酸检测,比普通人要严格一些。
考虑到露宿者们在隔离点内可能会有一些情绪问题,我们和风社工又常年为西城区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提供服务,于是从2月9日开始,我们就每天往隔离点跑,做一些沟通安抚工作。
里面有一些熟悉的面孔,打起交道来也相对方便。也有些以前没见过的,但并不是新的露宿者,而是以前没有发现的。
最近关于滞留在外地的湖北人变成“新流浪者”的消息比较多,我们在隔离点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不一定是湖北籍的。
因为每年过年的时候北京会有大量的人员回老家,有些需要用工的餐馆或者工厂就会出现一个空窗期。一些人就在这个时候来北京打工,今年刚好是在疫情暴发之前“逆行”到了北京。
很多人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就是去小餐馆干体力活,结果来了之后疫情就暴发了,到处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办法返回老家。
会在这个时候舍弃和家人团圆的机会来打工的,本身经济条件也不好。为了省钱,有些人就去露宿了。我们去通知可以来隔离点的时候,他们也就很配合地过来了。
我们在隔离点的工作主要就是安抚大家的情绪,因为总有人想出去。普通人在房间闷十几天也会觉得很不舒服,何况他们大多常年不住室内,无法习惯封闭的环境,精神压力很大。
他们不少人也不了解疫情的情况。有些人会谠我要出去打工了,手上没钱了,在他们的经验里,开春了就能找到一些零工了。还有人说自己在外面还有朋友,要去跟他们交代一下自己去哪里了,或者就是要出去透透气。
我们也只能反复告诉他们外面的形势,依旧没有什么餐馆开门,疫情也还没有解除。另外就是陪他们聊天,让他们把闷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一起来规划未来隔离结束后的路径。但如果遇到实在是想出去的,也只能拿14天隔离期没过的硬标准来拦他们了。
其实我们日常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新面孔,想破冰都是很难的。碰到会抽烟的人,我有时候会点上一根烟,大家话也变多一些了。但是在隔离点穿着防护服,连这个办法也无法用了。更何况,隔离点还是禁烟的。为了提醒大家记住不能抽烟,潇哥会装作借火,等到把打火机要过来,就换成另一副面孔:“这里不能抽烟的!”
14天的隔离期结束后,是去托养机构、回老家,还是再回到街头,还要看露宿者自己的选择。之前我们也不知道究竟会怎样,会不会有很多“强制”,但好在最后他们还是有的选。
隔离点会给我们提供防护服,应该是卫健委那边送来的。每天下班后,脱下衣服反复消毒才会回家。得知要来隔离点工作的那天,家人还是挺担心的,但是也不会阻止我们。
我们同事之间,也会觉得这似乎是件很平常的事情。虽然有危险性,但都已经防护到这个程度了,还能有什么不干活的阻碍吗?我们是一群平时照顾露宿者的人,应该也能照顾好自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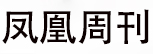
 凤凰周刊
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