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再度宣布紧急状态,国民寻求出路
“我在找工作的时候,从没想过要当巫女。”
新年第一天,24岁的日本女生佳奈穿上传统巫女服饰一一小袖(白衣)搭配红色绯祷(裙子)并佩戴头饰,在福冈县宗像市的宗像大社招待前来参拜的客人。在日本,巫女作为神社神职之一,不仅可接受神的凭依,传达神的意志,还担任着祈祷、驱邪、祭祀的职务。
高中就立志当空姐的佳奈去年大学毕业后,顺利入职日本航空公司(JAL,下称日航)。按计划,她从去年4月起应先在福冈机场从事地勤工作。然而当月16日,日本首度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原计划在羽田机场举行的入职仪式被迫取消。佳奈和另15名同期入职的新人未上一天班,就被要求在家待命一个月。
这之后,地勤工作有所恢复,但持续低迷的航空业让佳奈这样的一线员工并没有太多工作可做。公司开始向有合作的地方城市进行借调,前往宗像大社成为她最后的选择。
1月7日,日本首相菅义伟正式宣布,首都圈的东京都、琦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再次进入紧急状态。为了把防疫措施的影响降到最低,日本政府采取部分有限度的措施,包括要求餐饮店缩短营业时间等,学校、影院和剧场则将继续开放。但这依然让外界担忧,日本能否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员面影响并举办东京奥运会。
“共享员工”模式流行开来
福冈县宗像市的宗像大社供奉着守护航海安全的女神,是日本数千座宗像神社的总社。每到新年,有众多参拜者来此祈祷航海安全和交通安全。
为了迎接新年参拜,宗像大社从去年12月21日起就开了巫女研修班。“一共有31名来自日航的地勤人员到我们这里当巫女。”宗像大社的一名负责人向《凤凰周刊》介绍,“从1月1日到11日,每天11人进行轮换。她们会和神社原有的31名巫女一起工作。”
在巫女研修班上,这些人会学习神社使用的语言、了解神社的历史、背诵护身符一览表,并学习如何穿戴传统巫女服等。而空姐想要成为神职人员仍有着最低要求:必须是身心健康的未婚女性。
年末,距离上岗当巫女的日子近了。佳奈在家一边看30种护身符一览表,一边背诵它们的名字以及价格——付款要叫“初穗费”,表达感谢不能直接说“谢谢”,而要使用神社特有的措辞。
“我们没有特意让客人知道她们是日航的员工,客人会将她们看作和其他巫女一样。”上述负责人说,受疫情影响,来宗像大社参拜的人数比去年少了四成。“从12月开始政府就呼吁大家分散参拜,所以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四年前,日航与宗像市签订了“助力解决地方友展”的合作协议,如今帮到了自己的员工。新冠疫情之下,日航提出向宗像大社派遣员工,员工可签订短期借调合同,日航从宗像大社收取“服务费”。
公司内部第一次招募时有超过100人报名,包括佳奈在内的31人面试成功。还有日航员工前往宗像市著名观光景点“风车展望所”进行除草、修整土地和种花等工作,或是在福冈机场卖宗像市的农产品和水产品等。
随着抗疫形势再度严峻,加上英国变异病毒入境,日本全国范围内的“Go To Travel”补贴旅游计划被暂停,航空业也只能继续低迷。

日本亚洲航空、廉价航空公司(LCC)等均陷入艰难境地,甚至启动破产手续。国内外航线大幅减少,空乘的乘务次数减少到平时的五成。不少航空公司表示,裁员为当务之急。
停航期间,身穿制服的空乘们戴着口罩,在成田机场附近的农田种植向日葵,将其赠送给34所小学。为了减少航班和人工费,各大航空公司将空乘人员暂时借调去有合作协议的家电销售店、呼叫中心、物流公司等。除了短期借调,也有长期派遣。日航从2020年8月起陆续将员工派往北海道和福冈县,负责当地旅游开发,任期长达2年。
因疫情催生的“共享员工”模式正在日本流行开来,受冲击较大的企业将员工“共享”给其他人手不足的企业,一方面可以维持雇佣关系,一方面也给这些员工创造了新的谋职机会。
最近一段时间,知名电器连锁企业野岛电器从航空公司招募了300人,从东横INN酒店招募了300人;保圣那人才咨询公司招募了来自航空、旅行、酒店行业的员工近千人;永旺旗下的永旺零售从居酒屋企业Chimney招募了45人,其中10人最终签约成为正式员工。
上班族闲暇时做起副业
疫情也促使更多日本人开始考虑副业。日本去年的畅销书中包括各类手把手教你干副业的内容,例如《赚钱的副业图鉴》《人气副业排行前30》等。“一边工作一边每月多赚10万块的副业有哪些?”“2020年推荐给上班族的9大副业!”等话题频频在网络上成为热门讨论。
日本最大贸易工会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RENGO) 2020年11月19日至26日实施的问卷调查显示,认为2020年工资未受疫情影响的受访者只占四成,有近六成的人表示收入减少或难以判断。
为了弥补工资损失,副业时代就此到来。“把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都投入到社交媒体的运营土,一个月多赚了40万日元(约合2.5万元人民币)。”在IT咨询公司工作的福田因疫情在家工作,以此为契机开展起他的副业。
客户反馈平台TrustYou实施的“日本疫情之下的工作方式”调查显示,受远程工作影响,43.6%的人认为“副业变得容易”,54.8%的人表示“今后会增加副业”,43.3%的人表示“对副业热情高涨”。
在日本,大部分企业出于担心机密泄露、影响本职工作、过度劳累等原因,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禁止副业”。直到2017年底,日本才开始在政府方针上尝试为副业兼职松绑,逐步放宽就业规则的限制。
疫情开始时,突然开启的远程办公让不少上班族感到困惑,当他们逐渐习惯后,便尝到自由支配时间的甜头。可支配时间增加,最重要的是节约了通勤时间。“工作的地方”和“休息的地方”界限变得模糊,对于“闲暇时间做点什么”的想法增多。
“疫情下公司销售额大幅下降,我们无法再接收新员工了。”去年11月下旬,兵库县立高中的指导老师接到一家当地食品制造企业的电话。一个多月前,该校一名高三女生拿到了该公司的offer,原本期待在2021年春天入职,现在却泡汤了。
在兵库县和大阪等地,高中生求职被限制为“一人一社制”。也就是说,原则上一个人不能获得多家公司的offer。这意味着,这个女生必须重新开始找工作。而到了年底,面向高中生的招聘会早已结束。该校指导老师担心,今后这类事件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失业的演艺界人士被迫转行
疫情期间,日本社交媒体上关于“Uber Eats帅哥变多”的讨论越来越多。Uber Eats是叫车服务公司Uber旗下的一款食品配送应用程序。
听到这个消息,一头黄发、头戴鸭舌帽的舞台剧演员长沼薰不禁笑了。他在去年10月注册了Uber Eats:“疫情使我精神状态十分低落。有演员朋友劝我试试这个,一开始我有些抵触,但想了想,不合适停了便是嘛。”
一个多月来,长沼薰瘦了7公斤。他每天蹬着200日元租来的自行车在居住地附近送餐,“就像在街上探险一样”。据他说,一旦想耍休息或有其他要紧的事,可以随时停下来。“我和剧团伙伴计划在今年1月举办一场舞台剧,因此经常需要开线上会议。送外卖有一定自由度,对我来说是合适的。”
“但其他同行或许会担心送外卖时遇到粉丝,被拍到狼狈的样子,所以不愿尝试吧!”他笑言。
疫情之下,不少演唱会、公演、节目纷纷被叫停,餐饮成为不少演艺界人士的副业,但当日本宣布再度进入紧急状态,连经营餐厅恐怕也变得艰难。
东京文化财产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截至2020年12月13日,受新冠疫情影响中止和延期的歌舞伎等传统表演艺术公演超过4300场,据推算,损失额将超过170亿日元。从2020年5月开始,有四成以上戏剧演员、歌手、舞蹈演员等没有收入,七成以上没有新工作。
2020年3月5日,著名演员西田敏行以日本演员协会理事长的身份致信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要求政府提供支援以保障剧场和影视行业演员们的生活。他在公开信中提到,“很多演员因谈不妥违约金陷入生活窘境,或是未与企业签订协议因此无法成为政府补助的对象”。
然而,公开信没能让艺人们的生活好转,不少人只好在网上卖演唱会的T恤、毛巾、贴纸等周边产品。一位剧团演员说:“生活困窘的艺人甚至会在社交网站上说自己交不上虏租、电话费,还不上信用卡,请求粉丝支援。”
放弃演艺事业、跳槽的艺人比比皆是。一名摇滚乐队的吉他手剪了长发,转行建筑业。“年轻时在老家考了驾驶重型机械的执照,这让我能在疫情下谋求生路。最近外国劳动力少了,我也有机会上岗操作吊车。”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但我缺乏实操经验,如果打碎公寓玻璃就糟了。”
63岁的舞台剧演员平贺贯一选择了一家看护机构打工。据他说,2020年4月、7月、9月出演的三部话剧因疫情全部延期。近半年来,他作为演员的收入是零。
平贺贯一参演的《你不知道的契诃夫》原定于去年4月1日在东京公演,这部戏将俄罗斯剧作家契诃夫12部短篇作品进行了戏曲化处理,原本门票都售罄了。“最大的打击是,公演前几天突然被通知(演出)延期了。”他回忆说,剧团从2月开始排练,外界也非常期待,结果正好赶上紧急事态宣言的宣布,“很多演员都哭了”。
如今,平贺贯一在护理机构的月收入仅有3万日元(约合1900元人民币),连吃饭都难。此前,他曾兼职做过十年的影像器材保养工作。但疫情推倒了影视业的多米诺骨牌,连影像器材公司也没活儿了。
无家可归的人如何过活?
在找到落脚地之前,36岁的山本在宫城县首府仙台市的一个公园住了一周。疫情前,他在山形县一家温泉旅馆打工,这是一份管吃管住的工作。但去年4月疫情大面积暴发后,他就被解雇了。“刚来仙台的时候,我就睡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的时候,穿上牛仔裤、运动衫等六件衣服,盖上两条浴巾。下雨了就躲在台子下面,虽然很冷,但只能这样。”
另一边,60岁的加藤正在公园长椅上数着硬币:“这1400日元是我的全部财产,我想尽快找工作。因年龄原因无法做体力活儿。”疫情前,加藤在娱乐场所打工兼职做司机,月收入20万日元。最近因顾客减少,他也被解雇了。
幸运的是,山本、加藤最近住进了仙台市青叶医的支援机构“清流之家”。在一座简易钢筋二层小楼里,卧室、食堂、医务室、浴室和洗漱间等一应俱全。他们可以在这里免费居住三个月。目前“清流之家”的30个房间内住着超过40人,这里提供饭菜,是这些无家可归者最后的堡垒。
“清流之家”的负责人表示:“仙台是东北地区的核心城市,对工作和生活充满期待的人们聚集在此。但由于疫情,他们没了存款,付不起房租,没有可依靠的人,于是来到这里。”
此前在福岛一家工厂务工的木村同样是在去年4月被解雇的,再就业变得困难,因为“所有工厂都不再招聘了”。
这个寒冬,木村从家里步行3小时来到了仙台车站,赶上当地的救济活动。“我吃了三碗饭,喝了四杯咖啡。”他开心地对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则开玩笑说:“肚子好大啊。”他回应道:“还可以,只是五分饱。”
目前,他一边接受社会福利机构的救助,一边继续找工作。“虽然难找,但我必须要工作。我不会输给新冠病毒,会拼命努力的。”木村显得很乐观。
加藤入住“清流之家”一个月后迎来好消息,他被当地一家福利机构聘用为司机,负责为老年人开车,每天工作4小时,每周工作5天。“真的很高兴。接到工作后就数着还有几天上班。”加藤说。
在日外国人被剥夺感增加
同样面临矢业的还有大量在日本的外国人,他们被剥夺的不只是工作,还有回家的机会。
自去年5月开始,面向外国人的求职网站Gowell开设了免费咨询窗口,为这些人解惑。该网站公关部的柳川告诉《凤凰周刊》,因新冠疫情失业来这里咨询的外国人激增,每个月都在一千人以上,以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人居多。除了求职以外,他们主要咨询有关失业造成的生活和回国困难等问题,并询问在留签证和补贴申请等。
38岁的缅甸人敏明来日本学习IT已经十年了,前年进入一家地产公司做数据管理,并成为正式社员。但由于疫情业务下降,去年9月她被解雇了。“现在我主要靠失业保险过活。因为付不起房租,我只好搬离东京,找了更便宜的公寓居住。”
“由于签证限制,在企业工作的外国人法律上是不可以从事体力劳动的。”柳川举例说,但如果因疫情被解雇,在找到下一份工作前,可以暂时在餐饮店、便利店打工,限定为每周28小时以内。他遇到过在公司做翻译的外国人因疫情被解雇后在餐饮店打工的例子。
在柳川的印象中,因疫情失业而选择离开日本的外国人并不多,“日本法务省为外国人延长了在留期限,他们比平时有更长时间找工作。”
但对于外国人来说,更难过的是疫情扩大带来的不安感和没有冢人陪伴的孤独感。Gowell去年12月1日至19日对113名外国人进行过调查,75%的受访者认为,疫情让他们感到“更加不安和寂寞”。敏明说,以前和同事一起吃饭、工作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如今只剩下与遥远的家人通电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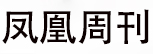
 凤凰周刊
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