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战争:平津沪宁小日子的幻灭

拿到1937年7月8日《北洋画报》的读者,会发现自己的眼前是一位裸背回眸的粉红佳人,皓齿微露,万种风情。这是头天晚上报刊编辑职工彻夜赶工制造出的八卦娱乐小报,《北洋画报》决定用这种活色生香的封面来庆祝自己的十一岁生日。
画报员工们当然不会想到,这将是这张报纸存世最后一个月,就在他们为报纸祝寿而彻夜赶工时,160公里外的一声枪响将会彻底终结他们所有的欢乐与希望。不
过此时,拿到报纸的读者所关注的,除了这位拥有完美脊背线条的当红影星的靓影之外,就是天津最豪华的光明影院将从当天开始连续三天上映的国产三角恋大片《
难姐难妹》。
即使实在与卢沟桥近在咫尺的北平,对这声尖利的枪响也表现出一种疑幻疑真的态度。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邓云乡早晨起来到槐里胡同的“临时商场”买了一只三星牙膏和一块力士香皂回家,“初夏光景,天气不太热,胡同中很安静,只是附属医院门口停着几辆等主顾的洋车”。邓云乡一边走,一边“孩子气地”看手里买的东西的花纹。就在这时,后面忽然来了一辆卖报的旧自行车,一边骑一边喊:“号外,号外,看日本人打卢沟桥的消息噢,看宛平县开火的消息噢……”
多年后英是注明红学家的邓云乡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认为这声号外的声音“一下子使我那闲适、出神的状态幻灭了”,《世界日报》上那个“头号铅字”印着的大标题上“卢沟桥昨夜炮声,日军攻打宛平县”几个“冒着火药味的字”,在他的眼前跳动着。但这种感觉很可能实在经历了漫长而残酷的战争生涯后对记忆的追补,而非当时的真实感受。
北平:只愿相信“胜利”的消息
真实感受,就像邓云乡回忆身边人的变现一样,“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院子中的邻居们自然是议论纷纷,人们总爱往乐观的地方想,有的幻想着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有的则认为宋哲元二十九军的大刀队一定可以打胜仗。”市面上也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正在暑假期间,大中小学都放假了,当时外地学生不少,大部分都已回乡了。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七七事变”五天后,《实报》还特意刊出了北平的物价,证明北平市民对近在眉睫的战火安堵如常:
“洋葱每斤铜元十六枚,柿椒二十枚,茄子十枚,洋白菜十四枚,韭菜台二十四枚,芹菜十六枚,回香十四枚,毛豆二十四枚,扁豆十二枚,土豆十四枚,西红柿二十四枚,大葱十枚,大白菜每棵十六枚。”
只有菜市上一条比较大的咸鱼,要卖二角多。
一位叫王焕斗的作家在7月19日写给友人的信中特别提到“单看北平的街面,绝对不像是战事发生了。电车虽然早归晚出,总没有停过。卖菜的、卖西瓜的照样儿
串着胡同叫卖。卖小金鱼儿的和卖花儿的,仍旧唱着音乐似的调子。”只有阜成门外偶尔传来的两三声不平凡的炮声,才让胡同里吊嗓子、拉胡琴的人一时沉寂下来
。即使是日军飞机发出的轰鸣,也不足以震动北平百姓的耳膜。就像往返于平津两地的记者范长江在7月25日的报道中所发现的那样:“七七事件后,日本飞机常在
平市上空飞行,市民看惯了,听到机声,也不甚惊异了。民二十二年塘沽协定时,平市实名初受外兵之恐骇,逃难者至多。今次则除少数优裕阶级外,中级以下市民
,普遍有了深一层的觉悟,日军进迫无已时,大家如果不能有办法,逃到那里也是问题。所以大家索性不跑,而且对于头上的飞机也若有若无的马虎视之”。
范长江形容普通百姓哪种“深一层的觉悟”,倒毋宁说是一种“可疑的兴奋”,混合着听天由命的无奈,暧昧不清的希望和自欺欺人的乐观。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外围战事的真相,无论是双方开战的胜负,还是内部谈判的过程,民众无从知晓。他们所拥有的只有各种不确定的消息。而这些消息几乎被人为加工成让人乐观的谣言。同样是报纸的号外。如果说7月8日的号外给邓云乡带来的是战争爆发的真实消息,那么7月28日的号外给民众带来的则是虚假的希望。汝龙在《这会是真的?》里惟妙惟肖地小写了一个头戴斗笠的“菜色面孔”的孩子,一边咽下大口的雨水,一边高喊着:
“谁瞧我这号外要不高兴,我就砍掉脑袋!”接过报纸的人“眼光只在上面瞥了一下”,就露出兴奋的神色:“喝,怎么回事?可不得了,占了丰台!这消息不会假,早晨就有了这传言了。哈——”
这个虚假的消息让北平城的普通百姓们陷入狂喜状态,“狂笑,高喊,一片尖锐的哄笑声浪,从这个屋脊爬过那个屋脊,夹杂着炮声、枪声、机声,奏起一种无名的音乐”,因为躲避空袭而沉寂的街道,也被这样一则乐观的谣言搅起一锅沸腾的浓汤。雨中行人忙着雇车将这个兴奋的假消息传递到全城各处,拉洋车的车夫也乐于拉着谣言四处奔跑,“这年头儿,您别讲价,坐上车爱给多少随您便。”一群朴实强壮的工人在雨天光滑的柏油路上蹲坐着,围着一位“鼻梁上架着一副大花眼镜的老者”,听他“慢条斯理”的重复这条报纸上的谣言:“我军今晨八时半克复丰台!”
“号外雪片飞来:进占廊坊,天津大胜,收复通县等等。连最好怀疑的人听到南京电台的广播也放心信任了”,被虚假谣言埋葬的北平城陷入了末日前的最后的狂欢。那些号称进城来“换防”的二十九军残兵败将也被捧为胜利的英雄:
“忠勇的将士!年轻人腿快,一口气跑到前门大街。喝!人如蝗虫样地挤成一堆,互相簇拥着,嘈杂地吵嚷着想挤到最前面去,大雨滂沱中,紧紧围着那群酱紫脸膛的兵士。这些硬朗汉子忸怩地受着众人的慰问,啜饮那些好心店伙送来的汽水梅汤,或畅嚼着大块的面包牛肉。”
吹嘘夸大本来是军中的常态,用于打发行军时的无聊和消除战斗前的紧张情绪,但这些受到狂欢情绪感染的残兵败将在民众面前大肆鼓吹的夸张事实,却被民众当成真相接受下来。他们“口沫横飞地述说他们的战场经历,怎样的一刀砍两个,怎样的将敌人的头颅削去一半”。听众们则对这些浮夸之辞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嘶哑的叫好。
这种不切实际的集体狂欢让经历过真正战争的士兵们也困惑不解,就像一位山东口音的士兵对同袍所说的那样:“不行了,我高兴得有点儿怪,我想弄把刀刺死我才痛快!”民众自动屏蔽了那些不利于胜利谣言的战败真相。当两个士兵惨笑着告诉别人:“一连人就剩了我们俩——”时,几乎无人对他们的坦诚做出正确的反应。
真实的失败的阴霾都被虚幻的狂喜驱散了。以至于第二天早晨,北平的百姓们看到二十九路军深夜撤退时留下的一地空荡荡的狼藉,仍然不愿相信昨日的胜利狂欢不过是假象。“那些蒙在鼓里的北平市民,依然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清晨,成群结队地等候报童将二十九军攻下丰台、廊坊以至于杨村、天津的号外送来”,恰如化名“春风”的作者在《九月烽火悼边城》所发现的,人们开始为这种剧烈的反差寻找一个合理的原因。许多人认定先前胜利的消息是真实的,但因为被北平城里的某位汉奸出卖,才被迫撤军。一些人开始咬牙切齿于在那个“姓张的”:“什么事都是坏在姓张的手里,从古来起,张邦昌、张世贵、张宗昌……恰好最近又有一位。”
人们无法从撤走的中国军队上再得到大捷胜利的幻想,因此只能乞灵于即将进城的日军残破衰相作为自我安慰的来源:“如日兵向我商家哭诉厌战,如载重汽车专运日兵阵亡头颅,如日军官佐于天坛自缢,如日使馆屡次追悼阵亡将士……诸如此类,映入市民耳目,能得无上安慰”。
其中传得最绘声绘影的,就是日军官佐天坛自缢的谣言,上吊自杀的军官从几人到十几人,再到“敌尸累累”。一位自称翻墙目睹真相的人宣称“最惨的是一个年轻军官,似乎剖了服又上吊的,手里紧执着一张纸片,上写:‘不愿再为日本人’。还有一个靠着一株柏树勒死的。就在他的身旁书上,刮去树皮,用钢笔之类写着一首绝命诗”,这个人不仅将这首绝命诗“翻译成七言绝句”,还补充说这名军官叫“田中诚一郎”。
无论是咒骂汉奸让所谓的胜利功败垂成,还是继续制造日军衰败厌战的谣言,都无补于北平已经沦陷的事实。

天津:最早的避难地
最有钱有势的人则早在开战伊始,就能得到前线最准确、最真实的消息,以便让他们做出最正确的判断。这些坐拥巨资和权势的先知先觉者是最先逃离的一批。他们的第一次目的地就是天津。
天津在被平沦陷的次日落入敌手。当北平市民们疯传天津大捷时,天津的民众也在陷入北平胜利的欣喜。“中国兵夺回了日本无理占据的新军站,东车站,围上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兵营和日本租界,东局子日本飞机场也被包围了,夺获了四十多架飞机”,刊载着这些谣言大胜消息的号外,在短短几分钟内就由一枚铜板涨到四大枚,但仍然供不应求。平津之间每天往返的火车将双方流传的谣言带到对方的耳朵里,从而又为眼药披上了一层真相的伪装。
但天津与北平不同的地方式它拥有大片西方租界。在华界,日本士兵可以肆意横行,但在租界却是一道屏障,将敌军暂时抵挡在外。从北平上车的逃难者,在拥挤的车厢里捱国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天津东站。这里距离租界区只隔着一座名为“法国桥”的钢铁大桥。制药通过这座大桥就是安全的天堂。从英租界的紫竹林码头就能乘船逃往山东、上海或是香港。
因此,天津在沦陷前后,至少在表面上海维持着一如既往的如梦浮世。天津的绝大多数娱乐场所都开设在租界里,而蜂拥进租界的避难者又为这里造成了一种浮夸的繁盛。“中秋节前后,街上满摆着鲜红的柿子,热烘烘的糖炒栗子和各种各式的月饼,车水马龙,大家忙着过节,丝毫没有山河变色的样子”。一位化名“须旅”的观察者发现,天津劝业场里排满了春宫图,专门出售给军旅无聊的日本士兵。
7月29日,八卦小报《北洋画报》出版了它的最后一期。封面上是北平当红舞星李丽女士搔首弄姿的含笑玉照。在这一期的软语格言中,报纸敬告读者“历尽艰苦
而没有成功的恋爱,是最伟大的艺术”,这究竟是一种自我安慰,还是一种自我辩护,仍然不得而知。但它最后一版的电影广告却不啻是对未来忧心的谶语。这天晚
上平安影院上映的电影时《贵族秘史》,广告词是这样写的:
“往来皆绅士,座上斤贵人,不闻枪声响,但见血染尘”。
北平和天津是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最先饱尝战火的城市,因此平津民众卷入战争时的心态,几乎可以说是其他即将被战火延烧到的地方百姓的“表率”。最初的议论纷纷、听天由命的镇定自若、枪炮声中的恐惧和沉默、被谣传的胜利激起的狂喜,以及沦陷后的自我安慰和苦中作乐,等等这些心态和行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战火迫近下的其他地方反复搬演。只不过对一个月后,被日军染指的第二个战场江浙沪的普通民众来说,这些心态上还要再加上一个“天真的侥幸”。

上海:侥幸心态的终结
战争对上海的市民来说,同样是突然降临的。一个月前,他们刚刚从报纸上看到七七事变和平津相继沦陷的消息。最初,他们还认定这不过又是一次“九一八”、一次“华北事变”,上海市长余鸿钧在8月8日虹桥机场日兵被杀事件后发表的讲话表示“中日双方都应该保持镇定,以防形势继续恶化”。驻守上海的将军张发奎受到西方记者采访时,他明确地表示上海不会受到日本进攻。当记者进一步追问他为什么不会时,他只是笑一笑回答道:“他们不会。”
“他们不会”不仅代表了上海政军两界的看法,也代表了上海民众的看法。尽管两者出发点并不相同。对前者而言,他们相信日本已经在一个月前占领平津,并且在华北地区大力推进,要消化这些新征服的地盘,建立傀儡政府,至少要像东北那样需要一两年的时间。他们的双手还不至于染指到江浙读取。日本的驻沪外交官一再向中方表示他们并不想扩大战事。船津辰一郎与高宗武在8月9日的会面明确提到“政府的方针永远是不扩大,当地解决。因此,我向就看贵国政府如何处置,或许能够很容易地局部解决。”这些来自日本外务省传递的缓和话语都相当于给上海刚刚紧张起来的局势注射了一针松弛剂。
对民众来说,六年前,“一.二八”事变的前车之鉴虽然仍在,但由于这一事变最后以停战协定的方式得以解决,所以人们相信这一次仍然可以得到“和平”的解
决。上海毕竟是世界级的摩登城市,是西方租界的所在地,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际的神经。日本人不止于冒西方列强之大不韪进攻这里。因此,除了一些敏感的
人发现日本侨民从7月23日开始就乘船陆陆续续大规模撤走,上海的市面上一切安素如常,摩登男女出入于娱乐场所,舞厅里舞步飞旋。
在这些上海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当然也包括考试。8月12日使上海各大学招生考试的日子。这天早上七点,一位叫沈祖礽的考生就抵达同济大学设在江湾镇
火车站对面的考场。八点钟,数学试卷发下去了。全场鸦雀无声,埋头答题。但到九点钟时,主考官突然进场宣布,数学考完后,其余各科考试不再继续,回家等候
通知。宁静的考场霎时鼎沸起来。又过了半小时,主考官再次赶来宣布:“因时局紧张,考试暂停,改日举行。”考生们不得不离开考场,前往对面的江湾过车站乘
车回家。
直到此时,他们才发现战火已经迫在眉睫。从炮台湾开往宝山路的火车已经全部被乘客挤满,售票口也关门了,火车站一片混乱。沈祖礽和大部分考生不得不用双腿沿着江湾路走到虹口公园,在那里乘电车回家。
炎炎烈日下,这些考生们大汗淋漓,衣服湿透,但纵使如此,沈祖礽发现他们的境遇仍然比那些肩挑行李、扶老携幼奔向租界区的难民要强得多。次日,中方军队开进上海,战斗开始。这场意想不到的战争终于降临在上海民众的头上。
就像在北平和天津发生的一样,早在七月底,第一批嗅到危险气息的富商和官员就已经携家带口迁入租界避难了。沈祖礽看到的这些迁往租界的难民已经是后知后觉,但仍比8月13日那枚落在大世界的炸弹爆炸后蜂拥进租界的人要明智得多。之后的事情一如平津的翻版。尽管上海华界整个浸泡在血海中,但前方记者频传的捷报仍然让许多人保持高亢的乐观情绪。
这种乐观一直维持到12月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为止。面对残留下的废墟和尸体,上海民众这才理解当初那种认为战争不会到来,即使到来了也持续不久的侥幸心理是多么的天真。日军并不会因为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会,在西方世界瞩目之下就畏首畏尾,对其心慈手软。所有先前侥幸的预估和判断都在“大道政府”的太极旗升起来的那一刻化为乌有。但这种侥幸心理并没有因之消散无踪,相反,它改变形态向其他地方扩散开去。

南京:一开始也平静如常
“南京虽然时时有炸弹袭来,然而南京的居民,却镇定得如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人一样”,《大美晚报》的记者如此报道日机空袭下的南京如何“平静一如往昔”。居民“现在是那么习惯于日本飞机的空袭了。几乎是每天,当四周响起了防空警号时,他们便满不在乎地躲入防空壕和地窟去,毫无慌张之象”。这段描述与一个月前范长江描述北平人面对空袭时的心态如出一辙。
与久经战乱威胁的北平不同的是,南京人这种安之若素的平静心态,被归功于南京极好的防空设备,“可算是全国各城市中最巩固的”。有“确切数目当然是无从知道,总之是许多许多架,是专门用来半路截击来侵袭的日本轰炸机”的驱逐机。
即使日本轰炸机没有被这些“很多很多架”驱逐机截住,设在城郊和各处的高射炮也会把它们射下来——首都庇荫下的南京居民的侥幸心理绝不亚于战前的上海。他
们相信最好的防御设施、军队都汇集于首都之中,政府是绝不会放弃首都的。他们绝不会想到四个月后,这里将化为人间地狱。
南京市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上海市世界级的经济都会,它们的侥幸是倚仗自己太过重要,以至于日军会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但与之相比,其他地方的侥幸则是因为自己太不重要,所以根本不会引起日军注意。丰子恺居住的桐乡石门镇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当上海正遭受累日轰炸时,丰子恺正在家里大排寿宴,宴请宾朋。“真的!炸弹很贵,石门湾即使请他来炸,他也不肯来的!”“他们打到了松江、嘉兴,一定向北走苏嘉路,与沪宁路夹攻南京。嘉兴以南,他们不会打过来。杭州不过时风景地点,取得了没有用。所以我们这里是不要紧的。”这种侥幸中甚至还有超自然的成分:“杭州每年香火无量,西湖底里全是香灰!这佛地是绝不会遭殃的。只要杭州无事,我们这里就安全”。就像前面所写到的那样,这番谈话的八天后,石门镇遭受首次空袭,17天后,日军杀进城镇。又过了一个月,12月24日,杭州沦陷。
不到最后关头,这种天真的侥幸永远不会打消。就像一个身染重病的人,他无法无视自己日趋加重的病情,但在最终诊断书下达之前,他仍有幻想说服自己仅是偶然微恙,绝不至危及生命。即使诊断书已经下达,他仍然可以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谣言和疑幻疑真的征兆让自己相信一切都在好转。直到无可挽回的那一刻到来,他才会选择接受这一切。
这种卷入战争时的心态很容易被从未经过战争的人视为自我欺骗,甚至用事后之明的视角,认定这种盲目的乐观和天真的侥幸根本是养痈为患。然而如果回到战争现场,就会发现对普通人来说,乐观和侥幸几乎是他们面对战争到来时的唯一选择。换言之,乐观意味着某种相信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信念,这是支持他们继续生存的唯一希望。
而侥幸,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只有大人物才有权有资格得到确实的情报,综合考虑作出有利自身的决定,小人物所能得到的,只有撒胡椒面一样的只言片语和不切实际的谣言,而且资金和物力都如此匮乏,即使他们做出最坏的打算,也无力付诸实践。他们只能直面现状,尽力闪避战争挥舞的镰刀,尽力活下去——乐观与侥幸形成了一层保护膜,在膜里面,是勉强维持的“正常”生活;而在膜外,则是战火的摧残和沦陷的耻辱。
这层保护膜是如此脆弱,只需要一把刺刀、一颗子弹就可以让它破碎消失。每个生活在战火中的普通人都不得不用这层膜将自己裹紧,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忍辱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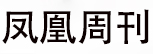
 凤凰周刊
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