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综艺节目凭什么那么火?
在“娱乐至死”的真人秀和歌唱类节目扎堆出现的潮流中,一系列以文化推广为主题的综艺节目突出重围,成为电视荧屏上的“一股清流”,刷新了观众对综艺节目的认知。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见字如面》三档火爆的文化综艺节目,出于同一位总导演关正文之手。他对《凤凰周刊》记者回忆道,如今火热的《见字如面》在上映之前内容就被看好,视频网站给出了高分,但对收视前景并不乐观。有同行甚至预测说,“这是一个小众节目,点击量20万就到顶了。”

2月19日,央视《朗读者》节目现场。
尽管关正文此前做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斩获了2014年几乎所有国内电视奖项,《中国成语大会》拥有5.59亿不重复计算的观众总量,取得平均收视率同时段全国第二的成绩,两档节目当年累计广告收益达2.4亿元,但《见字如面》的传播价值还是被质疑。
没有人想到《见字如面》会火,但腾讯及时发现了它的潜力,迅速给出了最好的宣推资源。截至3月3日,前9期节目网络点击量已超过1亿次,联合制作的各方实现了多赢。对于关正文来说,观众数字摆在这里,广告收入就不必再担心。
1960年出生的关正文,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怀抱着作家梦。他在作家出版社和小说选刊杂志社做了20年编辑,还参与创办过《长篇小说选刊》,后转战电视行业,成为著名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和导演。
他向记者透露,《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的制作灵感,源自互联网时代常见的“提笔忘字”现象。在节目制作之初,他的团队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一般成人对汉字的掌握和记忆程度,普遍不到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水平。而且,日常使用的语言也日趋单调和扁平化,“惊喜是‘醉了’,惊叹是‘醉了’,无奈也是‘醉了’。”节目组所面临的就是激活这些汉字、成语,让它们在大众文化生活中大放异彩。
《见字如面》则通过富有表现力的声音和表演,让被历史尘封的信件再度复活在舞台上。信件因其私密而具有历史真实性,能带领观众回顾已发生的历史,领略人物情状和社会风物。关正文对记者谈到,本来想做读书节目,但是自己没能确立经典图书化作片段内容传播时所能呈现的价值和节奏,所以选择了书信,“因为信独立成篇,节奏适合视频,且好的书信最能动人。”
作家梁实秋曾在《信》一文中写道,“书信写作西人尝称之为‘最温柔的艺术’,其亲切细腻仅次于日记。……(但)一袋袋的邮件之中要拣出几篇雅丽可诵的文章来,谈何容易。”今时今日,搭上爆炸性的媒介变革,似乎更是如此。为了挑选适合做节目的信件,节目组从全国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文学馆、博物馆、文史研究机构、名人故居、民间及私人信件收藏家手中网罗筛选,可谓大浪淘沙,时间跨度和内容广度都有着仔细考量。
被《见字如面》选中的书信,有萧红写给弟弟的《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蔡琴在杨德昌去世时写给媒体的《让他活在我的歌里吧》、刘慈欣写给女儿的《在时间之河的另一端》、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此点关系全部纲纪精神》、张爱玲写给王家卫的《很高兴您对<半生缘>拍片有兴趣》,等等。
其中,1983年,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以及曹禺的回信,在网上受赞誉度颇高。两位大师的交往故事跃然纸上。黄永玉坦率地说出自己对曹禺1949年以后的作品不满,“一部也不喜欢”,“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更犀利地批评“你为势位所误!”曹禺满怀感激地接受批评,还把这封信裱装进相框,挂在家中墙上,时时警醒。
来自台湾的演员王耀庆,将黄永玉对曹禺的尊敬、爱惜又不满表达得淋漓尽致,而张国立也将曹禺真诚的感激、谦逊和反省态度演绎得令人动容。两人情之所至,现场“飙戏”,让不少网友大呼“过瘾”、“声控的福利”。节目第二现场的嘉宾许子东点评道,这封信里的话是真话,这才算是真正的文艺批评,在今天很难再出现了,这是这封信现在被挖掘出来对于文艺界的意义。
黑龙江卫视《见字如面》节目,嘉宾张国立正在朗读信件。
如果说《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是将文化元素制作成更适合在电视上播放的短平快的竞赛节目,所以容易抓住人心、出效果的话,那么,《见字如面》《朗读者》这种节奏缓慢、娓娓道来的阅读节目获得成功,背后的逻辑似乎与之相悖——它们更像是瓦屋纸窗下的清泉素茶,没有花哨的背景,形式也简洁、朴素得不像是能夺人眼球的模样。两种类型的文化节目都火起来,它直指一个问题:电视机和电脑前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观众?
在这方面,关正文团队通过《见字如面》有了新的认知。目前,一般的网络综艺节目是45分钟一集,而《见字如面》是60分钟一集。在节目播出之初,不断有业内人士给出建议:互联网更适合碎片,剪辑节奏必须快,信息要密集,不然观众不买账。
这个意见被采纳,结果反倒抱怨声四起:“太快了,都来不及回味!解读还没展开,就出下一封信了。”
于是节目调整了节奏,从原来每一集读七到八封信,变成了六到七封信。关正文得出经验,“观众其实不傻。传播效率是单位时间里受众能接受更多的传播内容,这种效率的实现要分品种。如果是给大家带来复杂感受的节目,要从不同角度切入,带来有趣的认识价值,一味追求速度反倒会丧失效率。”这也似乎印证了观众不是想象中铁板一块的可被掌控和预料的“乌合之众”,简单看待互联网观众是错误的。
信息时代的车轮转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快,很多现象一时火爆,但可能还没来得及去细想趋势和辨别方向,就给市场判了“死刑”。始终以迎合市场为导向,而不注重内容品质,是要付出代价的。
知名文化学者杨早也有类似看法,他对综艺节目、影视剧中普遍存在的“就低不就高”现象很不满。他对记者谈到,《中国诗词大会》里的诗词难度设置还是偏低,当然,这可能有让观众获得心理优越感上的考虑。“但现在是分众时代,社会需求越来越多元。阅读书籍,观看电影、电视的受众都是如此。即便从商业角度而言,中国的电视节目还是做得太粗糙,没有投入太多智力和精力,去讨论怎样才能分众,怎样才能把握最想要的受众群体。”
针对文化综艺节目的持续红火,有人给出评论,“这是大众审美从想尝尝鲜到试图从整个网络空间的语境里逃脱出来的结果。”所谓网络空间的语境,就是追求速度、浅显和金钱。
这几档文化综艺节目的火爆原因是多样的,它们往往是火其中的某一期。比如,第二届《中国诗词大会》的受关注度远超第一届,央视内部对其重视程度也显著提高,在春节期间央视一套的黄金时间连续播出,这是很少见的。
有人甚至认为,第二季的火爆是在特定时间、特定政策窗口期的偶然事件。例如,据氢媒工场分析,第二季开播于1月29日,除2月5日、6日停播外,节目在短短6天内一口气播完。播出时间正逢春节假期,在满屏被中老年人视为轻浮的综艺节目和年轻人避之不及的养生节目中,以古典文化为内核的《中国诗词大会》,当然成了全家老少围坐一起看电视时的最大公约数,老少咸宜,收视率自然也就上去了。
彭敏是这类节目的老将,在他看来,一个电视节目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在节目过程中推出特别火的人物来,一个人的火和一个节目的火是相辅相成的。像《中国成语大会》第二季,就主推“白话灵犀”组合,把最后的决赛推向了高潮。而这次《中国诗词大会》,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推武亦姝,然后发现效果出奇的好。
“这些被推的人,首选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其次才是有特点的人。”彭敏带有一点自嘲,“反正不会推我,吃力不讨好。”
节目组对观众心理确有精心考量,比如,《中国诗词大会》的“百人团”中有很多儿童和外国人,这两者就保证了错误率。有的题目,观众在电视上看很简单,但现场在iPad上用极短的10秒时间答题是很不容易的,再加上十二宫格、九宫格的设置,有很强的干扰性,只要第一时间没对,基本上就不会对了。“虽然节目组故意这样设置,也知道这样错误率高,专家还是认真点评,说百人团怎么又错这么多,节目效果就这样出来了。”彭敏说道。
著名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大可,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则更强调学生家长在这股热潮中所起的作用。他指出,因为中小学语文教材出现重大改变,增加了大量古文内容,而家长对此毫无方向,于是,电视台古文类节目成为新的课堂。另外,在对传统文化经历了长期的贬损和批判之后,当局开始改弦易辙,推崇国学和儒学的价值观,“古文崇拜”体现了文化上的“政治正确”。
北大附中高三语文教师李杭媛,对记者谈起她看到的一些情况,文化综艺节目的火热,并没有让身边的学生对诗词有多少改观,尽管大多数人看了这档节目。“一个原本热爱诗词的人,看了节目可能会激发内心的共振和热情,但要让一个原本不热爱诗词的人,通过一个节目就热爱起来,这是很难的。”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现场。
一篇《请外行评委离开“中国诗词大会”:致节目组的一封公开信》在微信公众号上流传,也引起一番热议。该文指责节目组邀请的评委十分不专业,点评时在涉及格律、声韵等方面发生错误。其实,这背后也反映了一个矛盾,综艺节目需要评委口才好、反应快、幽默机智、有公众曝光度,大家喜闻乐见,这虽然和专业性不必然形成冲突,但要将两者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并非易事。如果请一个很懂诗词但口才和形象不佳的人来当评委,更是缘木求鱼。
杨早觉得板子打错了,应该打在节目组而非评委身上。节目本身既然希望能够给人一种权威感,就应该找顾问团队来保证专业性,或用后期剪辑等工作来进行弥补。“电视媒介有‘天花板’,它不可能去设计过深的东西,尤其是带有互动性的综艺电视节目,一定会采用一种浅显的、激烈的方式让观众移情、投射,过于高大上的节目必然收视率低。”
那么,这类文化节目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担传播文化的功用呢?杨早比较悲观,他认为,这些文化类综艺节目跟别的综艺节目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披了一张文化的外皮,或者说掠夺了文化的深层矿藏。他之所以批评《中国诗词大会》,并非觉得节目本身不好,这类节目的确能给受众带来欢乐、普及文化,但如果把节目的定位抬得太高,如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中华文明等,这种抬高会对公众认识“何为文化”产生误导。
杨早始终认为,观众想要在快餐化的综艺节目中获得所谓文化启迪,更像是一种幻觉。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注意力总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节目的火爆,其实也分走了大部分的资源,那么实际上留给大众从其他层面去关注传统文化的注意力就会减少。这是他对文化类节目火爆的警惕,也是一片叫好声中少有的“异见”。
本文节选自《文化综艺节目凭什么那么火?》,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8期总第60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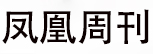
 凤凰周刊
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