鳗鱼数量锐减,在台湾水域捕捞海中“黄金”
天黑后,捕捞者戴着强光头灯涉水而下,一遍又一遍地在汹涌的海浪中撒网。
整个晚上,他们都在抖落渔网里的淤泥,挑出其中的宝贝:蠕动的透明鳗苗,一条还不如一根粉丝粗。它们的价值相当或接近于同等重量的黄金。
“有时是金子,有时是泥巴。”十年来一直在冬季捕捞鳗苗(也就是玻璃鳗)的戴嘉异说。玻璃鳗每年随洋流而来,吸引了几代人前往台湾沿岸,戴嘉舁这样的渔户就是其中之一。但这种吸引力正在衰减。“我们以前觉得这一行能赚钱,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那么确定了。”戴嘉异说。
全球范围内的鳗鱼数量都在锐减。环保人士称,买卖量最大的鳗鱼品种正面临威胁。台湾大学渔业科学研究所教授韩玉山表示,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过度捕捞、土地开发导致其水边栖息地丧失,加之近来的气候变化,台湾鳗鱼的数量已经在下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日本对鳗鱼的热衷,台湾鳗鱼产业得到蓬勃发展。但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2022年,台湾地区仅出口了价值5800万美元的鳗鱼。中国大陆早就超越了台湾,成为日本进口鳗鱼的主要来源。

韩玉山表示,虽然全球变暖对鳗鱼的影响还未得到仔细研究,但台湾渔民认为,温度变化会影响潮汐,从而影响他们的渔获。“海水越暖,鱼就会越往深处游,导致捕捉难度更大。”68岁的台湾区鳗虾输出业同业公会会长郭琼英说。
戴嘉舁这样的渔民会在宜兰县兰阳溪沿岸将鳗鱼卖给批发商,后者“收购鳗鱼”的牌子非常显眼。批发商的收购价高达每克(约六条)40美元,而黄金价格在每克63美元左右。
这些鳗鱼从这里被送往水产养殖场培育至成年。成年鳗鱼在被空运至日本等国家之前,还要来到台湾的最后一站,在包装厂里被放入装有沉重冰块的水袋。郭琼英在台湾北部的桃园市就拥有一家这样的工厂。
在这个由男性主导的行业中,她是罕有的女性。一个冬天的夜晚,她穿着套鞋在工厂里大步流星,和客户打电话,偶尔把手伸进池中抓住游动的鳗鱼,将其分类放人管道。
郭琼英是21岁入行的,当时进了一家经营鳗鱼等产品的日本进出口公司工作。她第一次见到鳗鱼,是在作为翻译参观一家包装厂的时候。看到工人们赤手就能抓住鳗鱼并准确判断其重量,她感到十分惊奇。
郭琼英在那家公司任职17年,因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失业。1992年,她自行创业,拿出全部积蓄购置工厂设备,还抵押了两套房产。她说,很多年自己都是在车里过夜的。最终,这样的勤俭换来了富贵的生活。郭琼英如今的座驾是一辆敞篷车,台湾媒体报道她的生平(称她为“鳗鱼女王”)。她曾做客一档日本电视节目,为评委们烹饪她的产品样品。“台湾鳗鱼赢得了比赛。”她笑着回忆道,“我们的鳗鱼就是最好的。”
在经常受到污染的河口捕捞鳗鱼就没那么光鲜亮丽了。渔民们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将篮子状的渔网一次次浸入水中,或用海滩上的金属船锚将自己拴住,然后游出更远的地方。陈志川是一名兼职技术员,有次差点在水中捞鳗时丧命。“我没力气拉住绳子了。我放了手,让自己在海上漂着。”他在兰阳溪边休息时回忆道。
“现在我年纪大了,经验也更多了。”陈志川说。他穿了一身绿色的橡胶连体服和一双黄色靴子。“我不会再把自己逼到那种程度。”说完他又扑人海浪之中。
他在这个捕捞季赚到了8000美元,尽管不如往年,但还是比较满意。疫情期间,因为餐馆关门,全球航运陷入混乱,鳗鱼价格也出现暴跌。
61岁的张世明年轻时曾在台湾西海岸的彰化市附近捕捞鳗鱼。上世纪90年代初,当地建起了一座巨型石油化工厂。大量烟囱排放出烟雾和蒸汽,附近的草地都被白灰覆盖。他说,捕捞的收获再也不复当初了。
“过去这些年,我们看到如此多的破坏。”张世明说,“今年的鳗鱼已经很少了。”至少,他听到的情况是这样;约20年前,张世明就转行做了劳动强度没那么大的蛤蜊养殖。他的大儿子就在那座化工厂工作。“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张世明说。
43岁的蒋凯德是一名兼职建筑工,多年来一直在打零工,直到有位朋友劝说他尝试以捞鳗为生。他从老家搬到兰阳溪边的一个村庄。他只能在周末与来访的四岁儿子和父母团聚。
事实证明,要精通这份活计很难,夜间捕捞鳗苗的收获也不好说,从10条到100条都有可能。最近一次出海,他的收获还不到20条。“很难赚到钱。”蒋凯德说,他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全家人都指望着我。”他说,自己快要放弃这一行了,“这么下去,早晚无以为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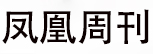
 凤凰周刊
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