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之下,我被澳大利亚地方旅游局裁了员
“极限运动胜地”“土著文化中心”“珍稀动植物天堂”······这些名号都集中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著名海滨小城一一凯恩斯。
这里人口只有15万,一年到头气候极为舒适,是前往世界奇观大堡礁的必经之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凯恩斯的旅游业发展蓬勃。每年4月,随着南半球逐渐进入秋季,这里总能吸引到不少海内外游客。但受到疫情影响,如今只剩下了空荡荡的街道与海滩,偶尔有野生动物来此玩乐。
突如其来的失业打击
2019年从国内的大学毕业后,我独自前往这座城市闯荡。不同于悉尼或墨尔本这些高度商业化的大城市,小镇上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走在路上,总会有入主动和你说声“Good day,mate(你好啊)”。
一个外国人想在澳大利亚找份理想职业还是有难度的,凭借十年来打下的音乐基础,我起初在一家酒吧找了份驻唱的工作。
某次演出后,我结识了当地警察Bobby。几次聊天后,他得知我曾做过摄影记者,又很熟悉旅游业,便为我介绍了一份当地旅游局的工作。
于是,我成为凯恩斯旅游管理中心的一名员工。这让我有机会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交流,带他们领略这片蓝色土地上的美景美食,不仅交到了朋友,也借着旅游旺季赚到一份不错的薪水,着实惬意。
然而,随着疫情的来临,这样的好日子也走到了尽头。
去年7月,一个稀松平常的早晨,我接到了同事Jane的电话。“我没工作了,Finn。”她抽泣道。Jane是英国人,今年60岁了。她几乎为旅游业奉献了一生,如果失去这份工作,恐怕再难找到一份薪水相当的活儿。
“怎么回事?他们有说原因吗?”我脱口而出,但联想到近期的情况,只能安慰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但很快我也接到了通知,包括我在内的16名员工都被辞退了。我所在的团队最多时有过几十人,如今只剩下上司和她的会计了。

“Finn,你做的很好,但我们······你知道的,最近真的很难,我也没有工作任务派发给你,我们甚至没有收到一个新订单。我知道你很喜欢这份工作,你真的做的很好了,希望疫情早些过去,你可以再回来的。”上司Selena无奈解释说。
往常我接到Selena的电话时,都会立刻从床上蹦起来,因为这通常意味着这会儿部门接了不少订单,特别忙。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和她通话,挂掉电话后我盯着电视发呆许久。不到半天时间,我就打包好行李,因为公司无法再向我们提供优惠住宿了。
启程前往布里斯班前,我开车回到曾经工作过的酒店City Palms附近,原本人潮涌动的海滩只剩下一个被遗忘的空酒瓶,吧台上也不再有那些谈天说地的旅行者;酒店几乎所有房门上都挂着钥匙,意味着无人人住。
走的那天,Jane来送我,她紧紧地抱住我,仿佛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之前加班的时候我们老抱怨“累死了,再也不想工作了”,但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原来这么让人不舍。
与国内不同,这个年纪的西方人大多依然工作,他们不太会去帮孩子照顾下一代。何况Jane目前是独身,只有工作才能使她快乐。她偶尔会去看望自己的孙女,但都只待很短的时间。失业的她将面临人生的新选择。
维珍空姐来酒店刷盘子
在疫情的冲击之下,澳洲颁布了旅行禁令,洲际之间也封锁了边境。这意味着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来访凯恩斯的航班基本都处于停飞状态,往日熙熙攘攘的凯恩斯机场一瞬间安静的可怕。
游客的缺失同样影响着航空业的饭碗。澳大利亚第一大航空公司一一澳洲航空公司(Qantas Airways)在一个月内裁掉6000名员工,包括1050位乘务员、630位工程师以及220位飞行员。下岗的不只是员工,澳洲航空还停飞了100余架飞机,据说节省的近150亿澳元运营成本让该公司尚能坚持一段时间。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第二大航空公司一一澳洲维珍航空公司(Virgin Airlines)就没那么幸运了。负债高达50亿美元、1.6万名员工面临失业一一面对如此重负,维珍航空不得已宣布接受破产托管。据报道,该公司于2020年9月被美国企业贝恩资本收购。
还没失业前,我在酒店后厨遇见了新来的姑娘Niort,她原本是维珍航空的空姐,在珀斯飞墨尔本的航线上工作了整整6年。失业后,她是靠着亲戚的关系才获得这份刷盘子的工作。
和我交谈时,她一直盯着手里的餐具,生怕它们滑落。“你有地方住吗?”我问道,她显得非常憔悴,像是很多天没有休息过。
“我就住附近,但马上又要换地方了。”Niort用手背蹭了蹭鼻子,没等我开口,反问说,“你有什么打算吗?这片区域都没什么生意了。”
“我或许会南下去酒厂找朋友,酒吧关了,但喝酒的人总归有的。”我回答说。
事实上,最后我也没去成朋友的酒厂,因为他的酒厂比我们公司更早裁员,现实隋况也比我想象的更糟。
据昆士兰州旅行局首席执行官Mark Olsen介绍,2020年,凯恩斯大约有1.1万人失业,出于对旅游业的依赖,该地区的经济复苏速度也会比其他地区慢得多。
“我们恐怕会是全国最后一片经济复苏的地区,过去一年预计损失了至少25亿澳元的旅游收入,这笔收入能支持13650个工作岗位。”Mark补充说。
不仅我所在的度假区域业绩遭受冲击,其他热门景点也难以幸免。
我的朋友Tom曾在大堡礁一带混得风生水起,他所在公司经营下40年的邮轮生意,旺季时的预约往往要排到几周之后。但疫情出现后,他只能收到要求退款的电话。
在墨尔本经营某大型旅行社的James更是叫苦连连。“旅行禁令之下,好几个月都无法营业了,即使之后恢复(营业),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他无奈地说,“除此之外,房租没有任何减免,贷款还得继续还,这条路真的很难走下去。”因此,James打算4月关闭旗下所有门店,只留一间办公室。
农场草莓只能烂在地头
对旅游业的现状,James有着清醒的认知,并逐步开拓其他领域。疫情期间,外卖需求猛增,他的蔬果团购生意有了起色。我作为首批遭遇裁员的旅游业职员,也只能琢磨其他出路。
被辞退的那段时间,刚好是当地草莓季到来前夕,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成了草莓农场的一名采摘工。
“早上6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中午有一小时休息时间。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休息,因为最后会按照你的采摘量来付钱······”第一天接受培训时,负责带我的监工还未讲完话,便跪在田间采摘起来。
作为监工,她原本的工作是记录我们的采摘筐数(防止有人偷懒),以及在草莓货车装满时把车子开走。但由于近期农场极度缺人,她也只能加入采摘行列。
澳洲的采摘工一般都是外国人,但由于最近的封城政策,没有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无法使用工作签证或学生签证入境,这让农贸市场遭受明友那了不小的打击。
放眼望去,地里的草莓一个个探出头,仿佛叫嚣着“你快来采呀”,却始终无人问津。算上我和监工,也就十二三个人在几亩地里游走着。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果实要么被雨水打烂,要么烂在地里。
草莓采摘工作十分辛苦,这也是本地人不愿意干的原因之一。草莓棚过于低矮,只能采取蹲或跪的姿势前进,才能看清草莓的位置,同时以最快速度采下放入塑料筐里。
午休时我认识了Lynette,她留着一头红发,两年前从意大利来到凯恩斯做调酒师。“以后有什么打算?”我问道,或许是因为自己充满迷茫,每见到一个新朋友,我都会这样问。
“活着就很好了。”Lynette用手指拨弄了—下三明治,用打趣的语气说。谈话间,我得知她在法国的祖母最近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的消息。
“奶奶上个月还和我说,等疫情过去就来看我,想让我带她去黄金海岸晒太阳,还有喝我调的LLB(一种酸甜口的调制酒,当地人最爱的饮品之一)。”说到这里,Lynette的笑容有些僵硬,讲话速度也慢了。
“或许她去了更好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黑暗,充满了阳光。”我不知道当时表达的是否准确,但希望能安慰到她。
一小时的午餐时间,Lynette只用了10分钟便吃完了整个三明治和半块炸鱼排,她戴上黑色宽檐帽,和我摆了摆手,又指了指草莓田的方向,大步离开了。这一刻让我觉得,生活会一直推着你向前,连难过的时间都不会留给你太多。
一筐草莓折合人民币9.4元,老手一小时能摘十来筐,但新人能摘上4筐已经是极限了。刨开休息和打包环节,10小时我总共摘了30筐草莓,获得了约280元人民币的报酬,同时还有磨烂了膝盖部位的牛仔裤和被雨水打湿的上衣。
一整天只能赚到过去2小时的工资,想来有些苦涩。作为草莓采摘工,到了下雨天也不能休息,反而要加快采摘速度。结果没撑过两星期,我就感冒了。老板担心万一我咳嗽吓跑其他人,赶紧结了工资让我走人。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我在一位香港老板开的港式快餐店里找了份送外卖的工作。疫情期间到店客人不多,但这家餐厅主要经营外卖这块,收入还算不错。
平时我开自己的车送餐,每单7澳元(约35元人民币),不报销油费,每天包一顿饭。对新人来说,即使有导航,有时偏差的定位还是会让你在路上浪费不少时间。
那段时间,去掉油费和房租,每天只能买点打折的蔬菜、面包,一个月下来剩的钱偶尔能买瓶红酒解解闷儿。
餐厅厨师阿哲帮了我不少忙,他是个左撇子,厨艺精湛,除了会帮我整理分类好单子和标签,每次还在我的晚餐多加一些蔬菜和肉。
自打从香港来到澳洲学厨,5年间他只回家过一次。“机票太贵了,家里人也清楚你在这边赚钱不容易,物价高,房租贵。”说这句话时阿哲正在切小米椒,兴许是辣味的刺激,让他的眼睛有些泛红。他手上的旧刀伤一条条鼓起,像是剪断的毛线。
海外旅游业尚难迎来春天
平日靠打零工勉强度日,不如回国家里蹲一一当时很多在澳的中国人都有着这样的想法。
澳大利亚的国际旅行禁令自去年2月公布以来不断延长,最近一次宣布延长至今年6月17日。解禁之前,本国国民无特殊情况不得离开本土。而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面对回国的天价机票,也只能望而却步。
在我的印象里,疫情刚发生后没多久,中澳关系恶化的新闻就不断涌现,外交部还屡次给出“谨慎前往澳洲”的建议。但相比身处“台风眼”的我,家人们似乎更加寝食难安。
其实我过的还行,在各个城市寻找打零工的机会,偶尔还能接受社区送来的补助——两袋面包、两盒牛奶、一盒鸡蛋以及各种蔬菜。有次邻居家做了火鸡,给我送了一只烤鸡腿,我和室友立即配着生菜做了几个三明治。
但在我母亲眼里,这些“被救济”的日子并不光彩。她不断打电话来询问最近的机票价格,并称要打钱给我。
最终我没有接受家人的好意,而是从朋友那里筹到了回国的费用。45921元——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张机票的价格。当我按下“确认付款”的那一刻,感觉心里被装满了,也被掏空了.一装满的是能立刻回家的喜悦,掏空的是这几年逐梦自由的那些瞬间。
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后,我终于回到了这片熟悉的土地,住进了隔离酒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靠在酒店的窗户旁,这样想着。但处于“寒冬”之下的澳洲乃至整个海外旅游业,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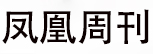
 凤凰周刊
凤凰周刊
